
- 专栏名称:我的这一年
- 作者: 度度
- 简介: 年近中年的陈徊,由于偶然的原因,打断了平静的家庭生活,陷入了一段始料未及,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上演了一场家庭、友情、爱情和职业相互交织、刻骨铭心的戏剧人生。她经受了情感洗礼,也阅尽了人生百态,并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西兰社会的众生相。短短的“这一年”,就像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命运轮回。

前言
我该跟你聊些什么
文/度度
十九小时后
见到久违的你
我该聊些什么
不必寒暄,不说变化
真巧啊
竟在这里遇到
找最热闹的地方
清清静静坐下
我要叹着气诉芬芳
把残酷编成笑话
我要仔细端详你
过分年轻或衰老
都会收到警告
我要你嫉妒我回忆细节的超能力
并且,刻意跳过那些
有你的情节
我要掷地有声
把够不着的人物事件
一一评说
告诉你晚霞正酝酿一场战争
把血腥的结局挂在了天空
我要言之无物
如空酒杯碰撞空酒杯
告诉你螺丝钉如何卸下武装
划破没有落款的信
酒过三巡,你如此清醒
而我,究竟该跟你聊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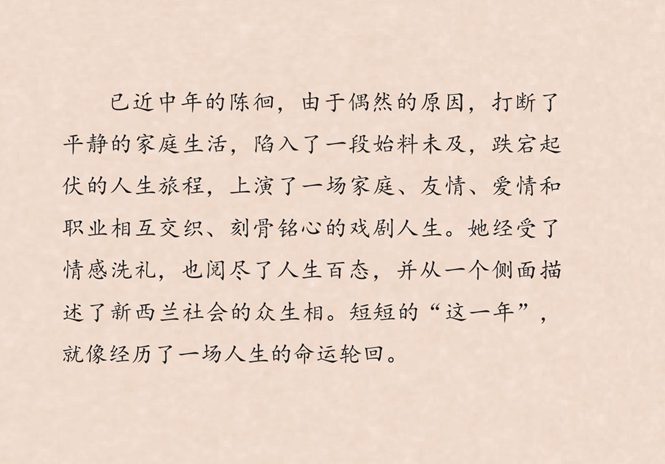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自己的一生,好像在某一段时间里就全部过完了,余下的时间就是在反复想念。
【第一章】
十字路口,待交通灯黄变红时,我踩下刹车。电话铃响起,屏幕显示何顿来电。
“嗨,我还有一条街就到了。” 我边说边把手机画面切回导航。
我听到电话那头觥筹交错的声音,背景音乐是 Lana Del Rey的 “Born to die(生而为死)”。
“好,我上去。”
车缓缓停稳。我又瞥了一眼屏幕,时间刚刚好。
今天是何顿公司的圣诞前聚会,每年这天都是我负责接他,偶尔还稍带上个把喝大了提前退场的同事。往年他们不是在酒庄就是在酒吧,今年的聚会地点却选了个偏僻的工厂区。路的尽头
有个高墙围绕的塔状的古老建筑,斑驳的铁楼梯漫不经心地斜搭在塔上,连接位于二楼的入口。
当我打开车门迈出去的时候,笑声透过虚掩着的大门传了出来。虽已入夏,夜里的风还是让我打了个寒颤。我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在那里感受到了我自己的温度。
我正准备走向的那扇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男人,他身后屋里的灯光把他的轮廓勾勒了出来,散发着柔和的光。我准备好笑容迎向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他缓缓从楼梯下来,等他再走
近一些,我愣住了——那是一张陌生的脸。
“你来啦。”那个男人站定,微笑地看着我。
“你是?”我一边瞪大眼睛,一边搜索回忆。
“咱们不是刚通过话吗?”男人举起手里的手机晃了晃,继续微笑。
我完全困惑了,摸出手机按下最后通话的那个号码,站在我对面的那个男人的手机应声响了起来。
我退后一步背靠住铁楼梯的扶手,低头看了看满是汗渍的手机,下意识地转身要逃。那个男人用他那极富魅力的声音叫住我,跟我说:“你忘了这个。”他走近我,微低着头,像要摘下起了
雾的眼镜似的举起手,从脸上摘下他的笑容递给我。我抬头看向他,他的面容渐渐模糊,好像乌云绊了个跟头,陡然从天而降跌落到我眼前。
我睁开眼睛,熟悉的天花板,角落里蜘蛛新结的网还在,新换的记忆海绵床垫还是让我的腰隐隐作痛。
又一阵笑声传来。
我坐起身,为无法继续刚才的梦懊恼着。梦里的后续情节发展吸引着我,比从厨房飘出的混杂着黄油和奶酪的香味更强烈。
今天何顿要去总部开会,罕见地没有早上班。平常这个时间,他已经坐在办公室,一手端着泡好的咖啡,一手忙着检查昨晚漏掉点赞的朋友圈。
厨房里,8 岁的胡图和 5 岁的西里正坐在高脚凳上看着何顿做早餐。烤面包土司制作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表情刻画”,
何顿拿圣女果一分为二放在烤得过于焦黄的吐司上当眼睛,然后抄起一瓶枫糖浆开始画鼻子和嘴。我跟他们互问完早安后就开始
打开冰箱准备胡图和西里上学需要自带的午饭。
“爸爸,我的眼睛没有这么大,我可以用 M&M 巧克力豆当吐司的眼睛吗?”西里指着圣女果试探地看着何顿。
“可以啊,”我接话,“不过嘛,”我拿起小刀,把手里的黄瓜切出两个三角块递给西里,“你这张吐司的脸上就得用这俩当鼻子和嘴了。”说完我往她的脸上猛亲了一下,一锤定音。
胡图看着他的饭盒渐渐被金枪鱼三明治、黄瓜条、酸奶、以及几块苏打饼干填满,愤愤不平地哼了一声问我:“妈妈,为什么我不能每天都吃麦当劳?”
“因为每天吃麦当劳会让你得病。”
“那我会死吗?”
“如果足够严重就会啊。”
“我会比别的小朋友都死得早吗?”
“有可能啊。”
“噢,”胡图如释重负,“那没关系啊,”他挑挑眉,“如果让我每天吃麦当劳,比其他小朋友死得早一点也没关系。”
我跟何顿同时转身互看了一眼,噗哧都笑了出来。
“可是,”何顿表情凝重,“你要是死了,你可就再也没法玩儿‘我的世界’的游戏了,而且,我会把你的玩具都送给妹妹。”
“那不行!”胡图大声抗议。
“所以啊,”我把饭盒扣好装进保温袋递给他,“去吧,把饭盒放书包里,中午不许剩饭。”
我每天的固定上班时间十年如一日地让我的车在日出后堵在早高峰的车流里,日落前陷进晚高峰的车流里。这份政府部门的工作——打电话、接电话、查资料、写报告,居然一干就是九年。
工作地点都换了三次,每次告知朋友我的新直线电话,她们都欢呼雀跃以为我终于挪了窝。很遗憾,我还在那里,同一张桌子面前,做着相同的工作。
这天上班时突然电闪雷鸣,从停车场到办公楼,走路一分钟的路程,我却像被人塞进滚筒洗衣机里按下了“漂洗”档。进了办公室,先到的幸运躲过这场雨的同事们远远地看着浑身湿漉漉的我,好像我身上还贴着“洗涤中,请勿关电源”的提示。一位同事从休息室端着咖啡经过我身边,刺鼻的香水味让我不停打喷
嚏。她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Bless you, and bless you x10 (上帝保佑你,上帝 10 倍保佑你)”。
我去休息室抓了一卷厨房纸冲进洗手间把自己从上到下用纸吸干,像根被吸干了油的薯条似的坐回座位里开始工作。
第一份报告刚写到一半,坐在我对面的同事泰瑞嗖地站了起来。她头上戴着通话耳机,一边跟电话里的人交谈,一边跟我做了个割腕和上吊的动作。我立刻起身走到经理马克的办公室,告诉他可能泰
瑞遇到了一位有自杀倾向的客人。马克迅速打开通话记录,里面显示泰瑞的最后一通电话已经持续了 23 分钟。他套上耳机开始同步监听电话,一分钟后,他在纸上写下:“泰瑞,确认客人的家庭住址,问她现在是否独自在家?是否身边有亲人?”
等我把纸条递给泰瑞返回马克办公室,马克又写好了第二张纸条:“泰瑞,问问客人准备什么时候自杀?用什么自杀工具?”
第三张,第四张纸条陆续传来,直到最后一张,“泰瑞,keep her talking (让她继续说下去)。”
同时,我拨通了报警电话 111,向警方寻求帮助。我提供了客人的个人情况,确认了客人独自在家并有立刻自杀的可能性。
警察联系了当地辖区的执勤警察,警察在 1 个小时之后带着心理辅导专员赶到了该客人的住所。
泰瑞一直等到警察进门才挂断电话,在 23 度的最舒适的办公室室温下,她大汗淋漓。
我给泰瑞泡了一杯她最爱的甘橘茶递到她手中,她感激地抱了抱我,转身看向正靠着隔离板的经理,“马克 , 为什么要问一个准备自杀的人的自杀计划?你这不是在鼓励她去自杀吗?”泰瑞不解。
“如果她已经告诉你她觉得人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你就要跟她讨论她接下来的打算。产生自杀的念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无处诉说。你躲避这个话题,就会让她觉得她更加孤独。”
马克皱了一下眉,好像对自己的解释不太满意。他看了一眼撑着下巴若有所思的我问道 : “陈徊 , 你觉得 Sympathy 和Empathy 有区别吗?”
“都表示同情,不是吗?程度不同而已。”我不以为然。
“你说得对,”马克点点头,“比方说,你看见有一个人掉在坑里出不来,如果你对她只有 Sympathy, 你就会站在原地对她说:‘我明白你掉在坑里一定很难受很辛苦吧,太不幸了!但是如果你对她有 Empathy, 你就会自己也下到那个坑里对她说:‘我明白你的苦,I am there for you (我在你身边)。’”
泰瑞擦了擦头上的汗,抿了一口茶,满意地说:“我觉得她会活下去。”
新西兰真的是一个对死亡无比热衷的国家,热衷到好像死亡都成了活下去的一部分,类似于寻找人生的意义一样——挣钱、养孩子、或去死。死不了,那就无比接近死亡。那些大行其道的极限运动,当你从悬崖一跃而下,脚上绑着的那条绳子就是你揣在怀里的那片后悔药——我只是去那个世界看看,若不好,我再回来和这个世界继续战斗。
实体书购买链接:点击
版权声明
1. 本文系新西兰天维网【天维伙伴】频道稿件,未经原作者授权,不得转载。
2.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3. 作者在本网站上发布的内容仅供参考。
4. 作者发表在本频道的原创文章、评论、图片等内容的版权均归作者本人或标注来源所有。
5. 所有天维伙伴签约专栏作者与天维网的合作,除非有特别说明,否则仅限于“内容授权”合作。